2023-01-19

邓伟志:社会学人要有“千里眼”


《邓伟志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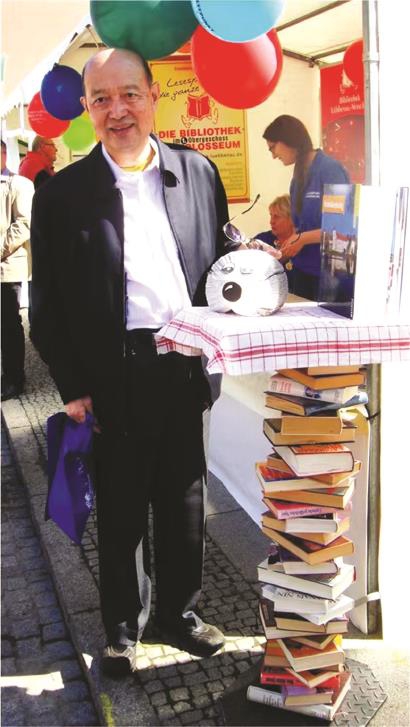
在邓伟志看来,“把钱用在哪里,都不如用在调研上”。他造访过全国40多个民族,全世界60多个国家。

在邓伟志看来,“把钱用在哪里,都不如用在调研上”。他造访过全国40多个民族,全世界60多个国家。

嗜书如命的邓伟志拥有24个书架。“我相信开卷有益,书读得越多,疑问越多,也就越能够做到对任何国家的学术权威尊重而不迷信。”
“我的人生的公式就是三个字,就是‘读’加上‘走’,能够化合为‘写’,经过思考以后就能化合成‘写’,一定会化合的。”回顾自己的学术人生,邓伟志用三个字这样概括:“读”、“走”、“写”。他嗜书如命,拥有24个书架,为了看不能出借的孤本还曾经在图书馆的狭小房间里住了一个多月。他用双脚丈量过五大洲的许多土地,全国56个民族,他造访过40多个;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他去过60来个。他更是以写为乐,几十年来养成了“三天不写文章手发痒”的习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再加上笔耕不辍的勤奋,这些人生经历最终化合为了一千万字的《邓伟志全集》,它被誉为“一部小型的中国社会百科全书”,记录着这位社会学家对真理孜孜不倦的探索,以及服务国家与社会的赤忱。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是邓伟志的毕生之所求。
学术档案
邓伟志,1938年生于安徽萧县,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系,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曾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未来研究会理事长、上海市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家庭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城市社会学。1981年,第一个在大学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教材连载。1984年,第一个提出妇女学,设计学科框架体系,在世妇会上被称为“妇女学奠基人”。聚焦中国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学人隽语
做学问不是靠运气。靠什么?我认为要靠“四气”。
一要接地气。接地气就是要知民、为民。学术研究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为了推进社会前进;不能搞空中楼阁,而是要脚踏实地地攀登科学高峰。
二要有书卷气。“道成于学而藏于书”。“知书”尔后“达理”。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的学人只有超过前人才是有出息的学人。而要超过前人首先要了解前人,学习前人。巨人的肩膀不是那么容易站上去的。巨人的肩膀是用书垒起来的。“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读书破万卷才能写出一卷。
三要有学术勇气。抓不到真理则罢,抓住了真理一定要勇于坚持真理,这是做学人的起码的品格。学术不是学舌。学人不能没有风骨。
四是要待人和气。学者对人,对任何人都和气,尊重别人的人格,口气不要有秽气。学者在意的是你的理论是不是让人服气,其它的皆等而下之。
——邓伟志谈“做学问靠‘四气’”(摘自《北京日报》,2014年2月10日)
对当今的社会学人来讲,重要的是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研究,创建中国本土的、可以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相媲美、相较量的社会学派。
创建中国社会学派,第一要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理论调整社会结构。第二要义是用社会化理论提升中国人的社会化水平。第三要义是用社会学之“矢”去射社会问题之“的”。第四要义是用社会学的科学方法对各类社会现象进行了解、说明、阐释和预测。
一句话,在社会学研究中,不能只满足于“看到”,更要做到“看透”“看穿”,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立足当下看未来。
——邓伟志谈“创建中国社会学派”(摘自《解放日报》,2021年5月11日)
【在社会学的诸多领域“领风气之先”】
1938年,邓伟志出生于安徽萧县。他的父亲投身于革命,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生活也因此贯穿了邓伟志的年少时期,但无论处境多么困难,都有地下党员来帮助他们转移,他前前后后共待过了一二十个村庄。他后来回忆说,这段颠沛流离的时光培养了他的适应性,“不管怎样艰苦,吃野菜、吃麦苗,我都能适应。”
1956年,邓伟志进入上海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学习,1958年随校转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在他治学道路上,有三个导师对他的成长至关重要,他们分别是延安《解放日报》的编委、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杨永直,时任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的李培南,以及时任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的庞季云。“你们不要去当官,好好读书,当评论员。”“你们一定要沉到底,一方面读书,一方面要了解实际情况。”这些教诲,尤其是“沉到底”三个字,对他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0年,毕业后的邓伟志先后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边读书,边做一些基础资料工作,同时写些巴掌大的文章”,成了邓伟志的日常。他成天泡在资料室里如饥似渴的读书,还帮着资料员拆新到的一摞摞报刊,以“先睹为快”。他也是图书馆的常客,有次因为任务紧急需要查阅大量资料,他与另外两位学者直接住在了图书馆,在靠近黄陂路的一排房子里的一间宽2米、长10多米的怪房间住了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地看书。“我相信开卷有益,书读得越多,疑问越多,也就越能够做到对任何国家的学术权威尊重而不迷信。”他这样说。
1980年,邓伟志出于对“血统论”的否定,写了篇《家庭的淡化问题》发表于《文汇报》,为《新华文摘》转载。这篇文章得到了创办全国第一个社会学系的复旦分校校长王中的赏识,邓伟志也因此应邀到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兼课。从此,他便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志在用社会学理论为治理一个和谐、有序、美好的社会而献身”,也就此成为他毕生的学术使命。
作为我国第三代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邓伟志的身上有许多个“第一”,并在社会学的诸多领域均“领风气之先”:上世纪80年代重建社会学之后,他第一个在大学开设家庭社会学课,并出版《家庭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导论》多部家庭社会学著作;1982-1984年间,他首倡妇女学研究,发表专著并指导多部妇女学教材的撰写,被誉为“妇女学奠基人”;1995年,他较早地提出市场经济的正功能与负功能,倡导经济、社会“齐飞论”;并较早提出“学会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的十个关系”,提出“政府是为弱势群体而设”;进入新世纪,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后,他也是国内倡导和谐文化的第一批学者之一……他在科学社会学、家庭学、妇女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社会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等诸多领域里都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足迹,这些思考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也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勾勒了一幅生动的画卷。
直到最近,已然耄耋之年的邓伟志仍在社会学的未来发展贡献着思想火花:比如,在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他提出并建立一门“改革学”,为深化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他也关注当下的热点话题“元宇宙”,思考其对社会学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社会实践是社会学理论的富矿,只要我们遵循理论研究的规律去认真研究,就一定会从富矿中提炼出‘优质钢’来。”邓伟志这样说。
【“不创新,毋宁死”的理论勇气】
对于邓伟志而言,从事学术研究就是从事学术创新。“不创新,毋宁死”。这是他曾经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所坚守的治学态度的宣誓。
在2018年《文汇报》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对推进理论创新有何见解”时,邓伟志说:“通才取胜是当今出理论的主渠道。如今攻克任何一门学科的前沿阵地,都少不了运用多种的力量。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讲,对自然科学也要有所涉猎。大跨度的结合,容易产生大跨度的联想,容易提出大跨度的假说。”凝结其毕生思想结晶的《邓伟志全集》便是最好的例证——在这部千万余字的巨著里,从天文到地理,从历史到现实,从社会学到经济学,从妇女学到人类学,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邓伟志的学术涉猎极为广泛。在他看来,理论工作者应该“心有社会”,以社会为胸怀,社会有多广,社会学者胸怀就有多广。
因为对社会问题的高度敏锐,邓伟志一度被称为“四多学者”:“发表文章多,被各大报刊转载的多,新观点多,引起争议的多。”但理论上的革故鼎新之路也并不平坦。在邓伟志的学术生涯里,争议始终如影随形,以至于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我的名字叫邓伟志,我的号叫‘邓争议’。”
上世纪80年代初,邓伟志在《文汇报》连发《家庭的淡化问题》《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淡化当官心理——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三篇文章,篇篇引发争论。他也知难而进地写过一些“不合时宜”的文章,比如,在党史研究中出现不太尊重历史的问题时,他著文罗列了党史研究中的十种现象,批评“一俊遮百丑”“一丑遮百俊”,批评“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英雄爹好汉”等问题。面对争议,邓伟志却非常坦然,“做学问不可能没争议,争议也可以成推力,推动逻辑更严密,概念更准确。”“即使人家是吹毛求疵,也应当感谢人家花气力吹毛,感谢人家找出了‘疵’”。
邓伟志曾经说,几十年来支撑着他在出错与纠错中匍匐前进的,是受到了70多年前解放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把他送出战场的精神所感染。他说,“手中有真理的学者一定要以学者应有的锐气、骨气、浩然之气来战胜冷气、官气,不趋炎附势,不搞逃跑主义。”或许正是这种“越挫越勇”的理论勇气,让邓伟志在学界有了“思想界的男子汉”这一美称。
【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态度做学问】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80岁退休时,邓伟志出钱设了个“邓伟志教育基金”,奖励学生田野调查。几十年来,他也总是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态度来做学问。造访过全国40多个民族,全世界60多个国家,这些田野调查绝大部分都是邓伟志自费去的,他说,“把钱用在哪里,都不如用在调研上”。
对于邓伟志来说,田野调查常常是“摸、爬、滚、打”。比如,为了考察滇东南的少数民族,他需要摸着绳子越过急流,摸着铁索桥过深谷;再比如,为了到云南的麻栗坡看化石,他在哀牢山里骑马爬山,结果马失前蹄,从马头上滚进了山谷。这些“披荆斩棘”的田野调查让邓伟志对国内外贫困人口的生活有了深切体认,看到了许多让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情景——几十年前去云南独龙族时,他发现独龙族的男人穿不起短裤,而只能以木板来遮羞;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玻利维亚,当地人做菜没佐料,只能用小便晒干后的白碱当佐料……这些实地走访的经历让他“盯住民生问题不放”,他学术研究中的一大主题便是“为贫困人口呐喊,为均衡发展著文”,着力提倡民生社会学、贫困社会学、贫困文化学。有人因此戏称他为“贫困社会学家”,他不但不生气,反而以此为荣。
在邓伟志看来,调查是集作风、方法、科学与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这是他经常讲述的一个例子:去问十个老太太“儿媳妇好不好”,十个人可能都会回答“好”。那么很容易得出“100%的老太太认为儿媳妇好”这样的结论。但如果换一种方式再去问:“儿媳妇给你烧过饭吗?”“儿媳妇给你洗过衣服吗?”这个“100%”可能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他告诫后辈,社会学人要有“千里眼”,社会学研究中不能只满足于“看到”,更要做到“看透”“看穿”。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那是“害己害人又害国”的“懒政、懒学”。
【用生活的简单化换取知识的复杂化】
在《人比雀儿累》一文里,邓伟志曾记录了自己忙碌而充实的一天:清晨5点半,当窗外玉兰树上几百只麻雀的啼叫声打破宁静,他已经伏案工作了许久。7点半,他已经将写好的稿件抄好,请妻子上班时顺便放进邮筒。然后回信、读书,处理一天的工作。12点,他从冰箱里找到一些剩菜,加点酱油、麻油、倒上开水,泡进馒头,用三四分钟就解决了这顿午饭。下午外出开会。晚上8点,窗外又响起了麻雀归巢的“大合唱”,不久后鸦雀无声。而他又继续在寂静的夜晚中笔耕了三四个小时……
“晨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这样起早贪黑的一天是他几十年来学术生活的缩影。直到现在,邓伟志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现在我还是一大早就起来了,但到11点是不行了,10点还是可以的。”当年,《邓伟志全集》出版后,很多人问他“这一千万字是怎样写出来的?”他的治学秘诀是“三少”:“少一点拉扯,用别人串门的时间来写作;少一点扯皮,用别人以牙还牙的时间来写作;少一点娱乐,用别人打牌、看球、跳舞的时间来写作。”
邓伟志常常说,学者宁为学问所困,不为财富所累。为了学问,他的做法是用生活的简单化来换取知识的复杂化,“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浑身上下没穿过名牌,饭桌上没有好菜,常常是十来分钟就吃好一顿饭。家里的摆设也很简单,不必花时间整理。”他对青年学者也提出了同样的期望,他说社会学大门口的对联应当是“追求发财莫进来,要想当官走别路”。社会学人“要进一步的解放思想,但只有通过读书,通过实地走访,把精力用在了解国情和民意上,才能知道哪里有我们需要解放的地方。”
获得“学术贡献奖”的这半年以来,邓伟志不断接到祝贺的电话,但他每次都对朋友们说,自己“轻如鸿毛”。他将这个奖项看作是同行对他的鞭策,决心“以开放的心态继续参与思想碰撞,为社会科学奋斗到停止呼吸之前的一分钟。”